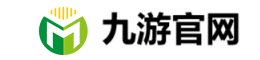中央再次对海洋强国建设作出重要部署。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并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系统部署。
会议强调,要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就在此次会议召开前,6月25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宣布“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项目全面投产,这标志着我国最大海上气田建成。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深海科技”首次被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与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并列成为国家推动发展的新兴产业,而“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项目的全面投产,正是我国在深海科技领域探索与发展的重要实践,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在新兴产业布局中向深海进军的决心与实力。
深海之下是一片资源富矿。其中蕴藏的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等战略资源的储量远超陆地,矿产中富含的钴、锰、镍等稀有金属是未来新能源和芯片产业的关键原材料。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到2065年,关键金属供应的35%—45%将来自深海底。
我国南海同样蕴藏丰富资源。3月31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在南海东部海域勘探发现惠州19-6亿吨级油田,“距深圳市约170公里发现1亿吨油田”话题迅速登上热搜。除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外,我国南海还有储量巨大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即有希望在本世纪成为油气替代能源的“可燃冰”。深海丰富的生物资源在医药和生物工程方面也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202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海洋经济呈现强劲发展势头,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8%。
虽然发展潜力巨大,但人类对深海知之甚少。即使人类的潜水器已涉足海底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在科学界仍流传着一句话:我们对海洋的了解还没有对月球的多。数据显示,全球仅有23.4%的海底被高分辨率测绘。海洋学家Katherine Bell团队5月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研究指出,在水深大于190米的深海,科学家肉眼观测过的深海海底面积不足0.001%,仅相当于比利时面积的1/10,而这部分水体超过世界海洋的95%。
对深海认知的匮乏焦虑始终驱使着人们向深海迈进,而深海科技正是人类了解深海的工具。“探索深海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只有科学技术上有了突破,我们才能了解深海,进一步为深海工程、深海资源的开发提供支撑。”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贾永刚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所谓深海科技,是以深海环境为研究对象,用于探索、开发和利用深海资源以及研究深海环境的一系列先进技术和相关学科的总称。
广发证券的报告指出,深海科技产业链主要包括上游的材料研发、零部件制造和通信设备,中游的船舶、潜水器、深海数据中心等各类深海装备,下游的深海国防、矿产资源开发、生物资源开发、能源开发、环境监测、深海探测、养殖等。
东吴证券的研究报告认为,深海科技包含四大技术方向:以载人潜水器、无人遥控运载器为代表的深海探测技术,以多金属结核开采、可燃冰开发为核心的资源利用技术,依托水声通信和导航系统的信息传输技术,以及耐高压材料、深海机器人等工程装备技术。
其中,“深潜”“深钻”“深网”组成的“三深”,是当前对深海进行科学探索的主力。载人潜水器(HOV)、有缆遥控潜水器(ROV)和自主式水下航行器(AUV)等为代表的“深潜”技术,可直接潜入深海进行观测、采样和作业,是遁入深海的“入场券”。但深潜最深只能到海底,从海底往下得靠钻探,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最大钻探深度可达11000米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便是“深钻”技术的集大成者;“深潜”的运行时间只能以小时计,“深钻”探索的空间有限,而“深网”则弥补了前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足,通过在海底布设电缆、联网传感器阵列,形成长期、连续、多参数的综合观测系统。三者结合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深海。
据贾永刚回忆,20世纪末进行海洋科考时,大部分装备都依赖进口,在“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引导下,深海科技开始了“追赶”之路。发展至今日,我国深海技术装备发展取得长足进步,许多技术已“领跑”世界。
从2012年“蛟龙”号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入海,到2017年国产化率达到95%的“深海勇士”号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的成功研发,再到2020年“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实现1万米极限深潜……在载人潜水器方面,我国已达到国际领先。
“在海洋工程地质环境观测技术和装备领域,我国科学家也在积极主导进行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的制定。”贾永刚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据介绍,去年11月,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与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ICGdR)共同主办了China Rock学术年会青岛会场,以“海洋工程地质与环境”为主题,推动海洋工程地质与环境领域的创新发展。
近些年,一个重要趋势也引起诸多业内人士的关注。中国相继研发建成“深海一号”“海基系列”“海葵一号”等一批大型深海油气装备,打造了“海洋石油201”等一批3000米级深水工程船舶,一批尖端装备研发实现新突破。
“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海上风电的发展,正助推一批深海科技成果实现转化。能源开发上下游涉及的深海科技,率先实现爆发式增长的潜力巨大。”从事无人船艇制造的珠海云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云洲智能”)总经理助理唐梓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今年5月,云洲智能V35A无人艇成功助力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深水海管铺设智能监测装备“海卫”系统完成海试,云洲智能自主研发的两级伸缩门架及张力控制技术,降低了高海况下无人艇姿态摇摆对水下光通的影响,首次实现了无人艇技术在深水海管铺设智能监测领域的工程化应用。
贾永刚团队也在积极向大洋矿区进军。2021—2022年,贾永刚团队工程师李凯携团队自主研发原位监测装备两次前往西太平洋,在锰结核矿区与稀土矿区进行原位探测、取样等工作。贾永刚团队工程师权永峥、鲁德泉等人最新研发的深海采矿羽流影响原位长期监测系统,将在中国五矿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和矿区开展采矿羽流影响示范监测。
“羽流可以理解为海底的沙尘暴,它究竟会对海底生态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观测,这些成果也有利于我们确立深海采矿环境保护标准。”贾永刚说。
虽然我国深海科技近些年取得诸多成就,国产替代率有大幅提升,但不少技术仍亟待突破。“一些看起来很小的零部件、元器件,如全海深水密连接器、传感器、浮力材料等技术,国产替代空间仍很大。”贾永刚说。
唐梓力指出,我国的声呐设备,如多波束测深仪等在数据获取的质量和分辨率精度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声音是深海传递信息的重要介质,多波束测深仪就像“眼睛”,可以透视深海,勾勒出海底基础地形信息,多波束测深仪的精度关乎深海探测时的“视力”,精度越高,科研人员对深海地形也就看得越清楚。
南通力威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南通力威”)总经理娄兴建认为,在深海采矿方面,需加快攻关重载化技术,实现400吨深海重载作业技术自主,从而帮助我国争取稀土、多金属结核关键矿产开发主导权。
“我国深海科技的起步晚于欧美,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从零开始研发需要时间。”娄兴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研发深海设备,需要“抢时间”,但也不能操之过急。深海环境复杂,一台装备必须反复多次海试才可验收。单次出海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不确定性较高,根据海况、距离,每一次出海试验时间不同,短则一周,长则数月。
“深海工程地质原位长期观测系统”便经历了非常曲折的海试过程。据李凯回忆,在2018—2021年间进行了5次海试,最长的一次近一个月。深海的高压环境,非常考验系统的稳定性和兼容性,过程中可能出现贯入系统卡顿、水下通信不顺畅等问题,需要通过多次海试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021年,该设备成功入选2021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对深海科技上下游企业而言,不只面临技术研发考验,还要考量商业化问题。南通力威自2015年将深海装备科技研发列入企业培育壮大的新兴产业,一边联合大连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组建“深海装备科技联合攻关”研发团队,多次承担省部级重大深海科技相关项目的研发及示范应用;一边积极开拓海洋资源勘探装备市场,地质绞车、温盐深探测系统(CTD)等产品已覆盖国内70%的新建科考船,锚泊系统在钻井平台、海上风电领域也实现了工程化应用。但娄兴建坦言,在深海科技商业化方面,面临成本高昂、验证周期长、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畅等问题。
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深海科技的背景下,3月,上海、深圳、浙江、厦门、青岛等沿海省市纷纷筹划并布局海洋产业发展。如上海印发《关于推动上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实施意见》,系统布局海洋产业升级和观测体系;厦门拟出台《进一步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科研创新、产业扶持等四方面加大支持。
“企业需要上场机会,进而在自由搏击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大浪淘沙,培育优势产业和技术。旺盛的市场需求和产品的不断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两端。”唐梓力认为,对于云洲智能这样的企业而言,急需政府开放应用场景,建设一批各种应用场景下的样板工程,通过小批量的采购,为整个产业链输血,保证产业存续,与此同时,加快出台配套的法规制度。
娄兴建认为,推动深海科技产业化发展,应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基金,设立深海材料、极地装备专项;构建产业生态,建设国家级深海装备测试场,降低企业验证成本;同时开放应用场景,推动国有深海装备在实船验证试验。
今年4月,海南省海洋厅表示,将依托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这一核心载体,开辟“以场带产、深海智造”新赛道,助力企业降低国际合规成本,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孵化。
高校在深海科技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聚集了大量技术人才,是技术研发的高地,载人潜水器起初很多突破性成就便源于高校科研团队,但高校难以兼顾装备后期的产业化应用。贾永刚认为,高校和企业之间需要深度融合,减少低水平的技术重复,以国家需求为引导,推动深海科技相关科学成果的转化。近几年,贾永刚通过专利转让和技术服务形式,成功实现多项科学技术成果转化。